
发布时间: Sun Jul 16 16:23:50 CST 2023 供稿人:詹晖
本文原载于《北京仲裁》2022年第2辑,总第120辑,本期责任编辑沈韵秋,本文作者:詹晖。
摘 要
商事仲裁被普遍认为溯源于欧洲的商人行会。然而,在中国古 代历史中某些时代,仍然能够发现商事仲裁的萌芽发展,首先是因 为某些朝代商品经济本身高度发达,其次是因为中国的法律历史传 统中民间调解和有某种终局决定民事纠纷性质的“调处”机制的存 在,最后是因为政府行政权和司法权集于政府,且一贯有“厌诉” 之情绪,故从古代中国的历史记载中仍能发现商事仲裁影子的存 在,这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必然结果。而商事仲裁的中国基因体现 于两方面:一是调解和仲裁的不可分离性,二是仲裁和官方授权存 在紧密的联系。
关键词
仲裁 古代中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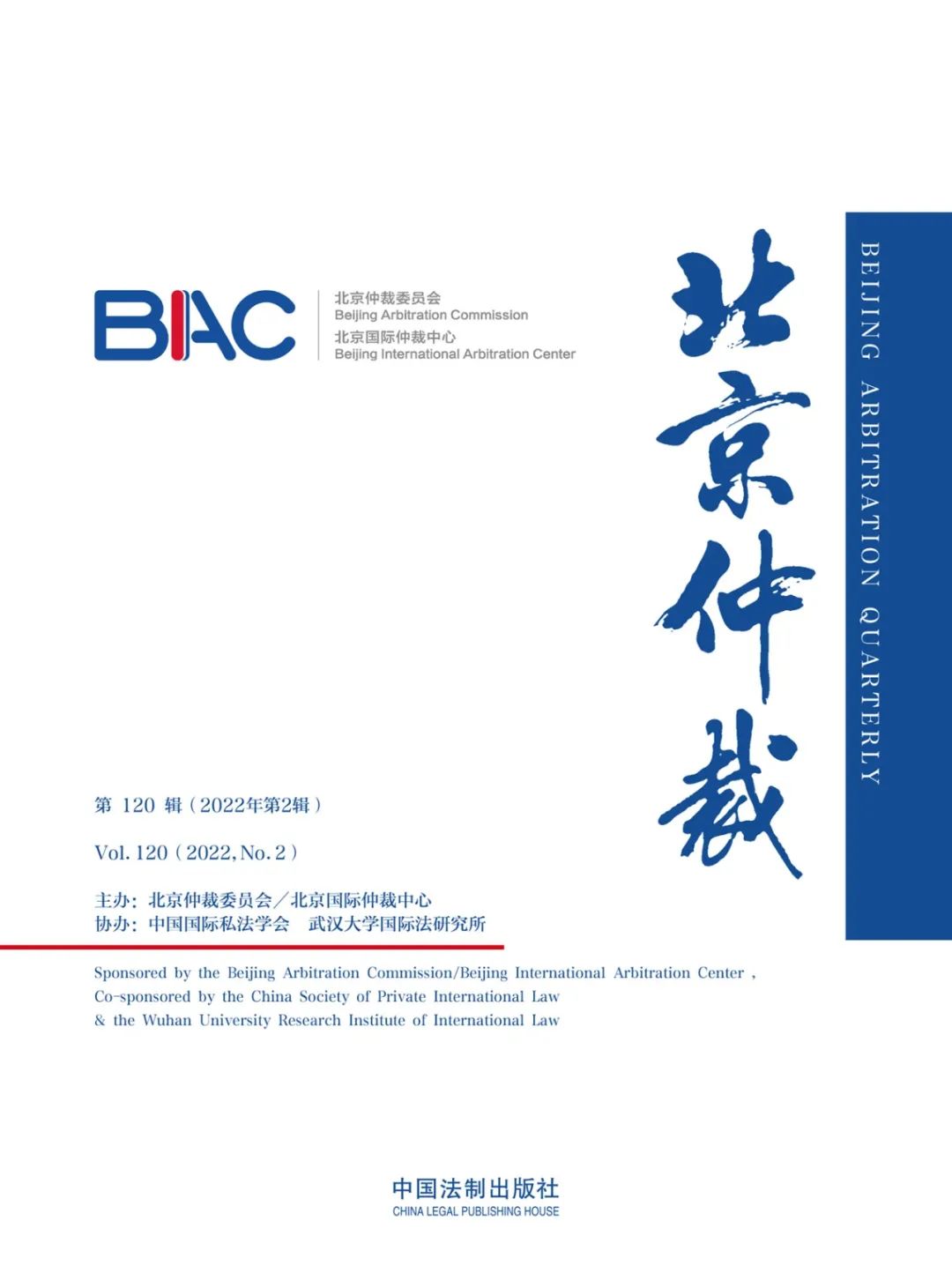
商事仲裁作为非诉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普遍认为溯源于欧洲的商人行会。当时的商事法院,包括市场法院、集市法院、商人行会法院和城市法院,性质上是非专业的社会共同体法院。法官和仲裁员多为在行会中有较高威望的人员,由商人们从同行中选出,或多数情况下直接由行会首脑和成员组成。当时地中海沿岸一带,海上交通和因此产生的海运贸易发达,商品经济取得了长足发展。各城邦和港口之间的商事往来增多,由此商人之间的商事纠纷亦逐渐增多。为及时解决商人之间的各种商事纠纷,也为行会之间的和谐和交易的正常进行,纠纷当事人自愿共同委托德高望重、办事公道、熟悉情况的第三人对纠纷进行居中裁判。因仲裁员的身份,采取仲裁的方法简便易行,逐渐为商人们所接受,形成了纠纷双方当事人共同约请第三者居中裁决其纠纷的习惯,并延续至今。
而古代中国虽然统治者大多情况下重农抑商,长期以来未能重视商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但是在历史的多个发展阶段,如唐宋、明清时代,因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人们已经有了多种商品和服务的需求,商品经济得到极大的发展,同样存在民间交易所产生的民商事纠纷的解决需求。
一、“调人”和“啬夫”——调解员和仲裁员的雏形
古自西周就有调人之官名,主要负责掌管调解民众纠纷。《周礼·地官》:“调人,下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调人的职责是“掌司万民之难而谐和之。凡过而杀伤人者,以民成之。鸟兽,亦如之”。但是历史典籍中并没有反映出调人职位的具体工作方法,而且调人的职责也并不是局限于民商事纠纷、经济纠纷,如《周礼·地官·调人》中提到:“调人掌司万民之难,而谐和之。凡过而伤人者,以民成之……凡和难,父之仇,辟诸海外;兄弟之仇,辟者千里之外;从父兄弟之仇,不同国;君之仇眡父;师长之仇眡兄弟;主友之仇眡从父兄弟。弗辟,则与之瑞节而执之。”这是在陈述古代的“移乡避仇”制度,杀人者遇赦免刑(过去经常有天下大赦),而被杀者家中尚有近亲属,为履行赦令,又防止仇杀,被赦者不得返居故乡,要移居外地落户,不同的仇恨,避的距离远近有规定,所谓和难,即指这种仇恨的和解,促进和平。
可见,首先,调人设置的主要目的是维持社会的和谐稳定,解决纠纷只是维持稳定和谐的手段之一;其次,调人调解的纠纷不仅仅限于经济案件,甚至可以说其调解的重点并不在于经济纠纷,而是以平民之间的刑事案件的解决为主要任务。
时间轴进入秦汉时期,随着中央集权制国家初具模型,中央越来越依赖于中央派驻地方的官员而不是分封的诸侯管理地方事务。“啬夫”出现了。“啬夫”一词本翻译成农夫,收获庄稼的人,在周礼中就出现了,《仪礼·觐礼》:“啬夫承命,告于天子。”但是职权不详,后到秦朝,掌管乡一级别的诉讼和赋税,但是是否具有公务员的身份,尚有争议。至汉朝,啬夫具备了正式的政府编制。《汉书·百官公卿表》中提到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汉书·百官志》中提到:有秩,郡所置,秩百石,掌一乡人;其乡小者,县置啬夫一人,皆主知民善恶,为役先后,知民贫富,为赋多少,平其差品。作为朝廷派驻乡里的最小行政管理单位,啬夫的主要任务是土地管理登记和收税,但是经县一级别的官员的授权,啬夫同样会处理一些民事纠纷。在出土文物《候粟君所责寇恩事汉简》中详细描述了一个民事纠纷中啬夫扮演的角色。建武二年十二月,客民寇恩受甲渠候的雇佣运鱼去觻得出售,议定付工钱一头牛和二十七石谷,但鱼价须卖够四十万钱。寇恩未卖够此数,卖掉作工钱的牛才凑足三十二万,还欠八万。于是粟君扣押了寇恩的一些车器杂物值。粟君告状寇恩欠牛不还。在这个典型的民事争议中,啬夫不但通过爰书(古代的取证文书)的方式对双方进行了事实调查和单独询问,同时也对于裁决结果向上(县)汇报了处理意见,后得到了上级的认可。最终查出原告方扣留被告方的财物已经远远超过了原告方的损失,原告的请求被驳回。
因古代中国政府行政权和司法权集于政府,一贯有“厌诉”之惯例,这个传统端倪于秦汉时期。所谓“厌诉”,是指只要不涉及赋税征收、土地和人口登记等行政管理、影响政府职权行使的职能,或者是因刑事案件破坏社会秩序的,政府往往怠于处理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纠纷,这就使“调人”和“啬夫”这些低级别的派驻人员虽然并没有官方裁判的授权,仅仅扮演着郡县长官裁判辅助者、调查者的角色,但是实际上在县、乡这个级别中出现的民事、商事纠纷,多是由“调人”和“啬夫”负责处理,因此认为“调人”和“啬夫”是最早的调解员和仲裁员的雏形,是没有问题的,可惜因为古代中国的历史记载均关注于典型的王侯将相史,对于市民生活的记载史料非常稀少,使得研究的素材缺失。
二、家族内、家族外和行会仲裁与调解的发展
随着秦汉确定的民事纠纷解决的思路,中国民间的私法纠纷绵延发展了两千年之久,民事纠纷产生后,交由族长乡里正式或非正式的公职人员处理,但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职业商人的出现也带来了一些挑战,中国式的行会仲裁也具备了生长的土壤。
家族内部的纠纷,包括户婚、田土、钱债、斗殴等产生的民事纠纷和轻微的刑事案件,都交给族长调解或裁决,清代又称“调处”。争议产生后,双方当事人各自邀请乡邻、亲友或在当地民众中有威望者出面说和、劝导、调停,若调停不成,则由族长或其指定的家族中具有威望的成员进行裁决,争议双方均必须接受这一结果。清朝大力倡导封建宗族的所谓“自治权”,《大清律例》规定,甚至连轻微罪犯、妇女罪犯可以送交宗族,责成宗族管束处理,而至于民事纠纷特别是婚姻、继承争端,也基本全部交给宗族处理。道光时期御史周作辑云:“每姓有族长绅士,凡遇族姓大小事件,均听族长绅士判断。”调处中的“处”,就不仅仅局限于需要两边当事人均同意的调解方式,而是具备一定强制力的裁决的方式。而家族内人员多已经习惯性地接受这种方式,如据《王孟箕讲宗约会规》载,王氏族人每月两次在祠堂集会,宣讲经书、伦理、国家法律等,然后处理各种纠纷。“一问族中有无内外词讼。除本家兄弟叔侄之争,宗长令各房长,于约所会议处分,不致成讼外,倘本族于外姓有争,除事情重大付之公断,若止户婚、用上。闲气小忿,则宗长使询所讼之家,与本族某人为亲,某人为发,就令其代为讲息。”家族调处的方式亦多次得到官方的认可。以在一个组织内部通过相对权威的人士进行调处,而其他组织成员服从这种决定,是成员能够成为组织的一员的前提,这样的逻辑跟行会仲裁的逻辑是完全一致的。
而在家族外的经济纠纷,仍然秉承着“无讼”的基本逻辑,依靠政府在乡里设置的官员处理,如里正、里长等最基层的组织,发挥着协调、裁决跨家族之间的纠纷的主要作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乡级别的官员虽然名义上属于公务员体系,但是大多数情况下其并没有获得过案件审理权的授权,无论民事案件还是刑事案件审理权仍在县、郡、州等国家机关,法律一般授权其有调解的权力,而调解不成做出最终结论的权力,仍然是来自各个宗族对其权威的共同认可,而非官方的授予,所以乡一级别官员只能说是行政上的地方管理者,经授权的调解员,同时扮演民间仲裁员的角色。如明代在全国各乡设立“申明亭”,法律明确规定:“凡民间应有词讼,许耆老里长准受于本亭剖理。”这种调处制度属于强制的诉前程序,不经调处而起诉的,按照“越诉”处理,经久无法调处的,方能进行起诉。而乡长、里长虽然没有审判权的授权,也在很多情况下通过调和处即调解和裁决相结合的方式化解纠纷,如两造当事人仍不同意,可以通过延长纠纷的解决时间,阻止当事人直接向县衙起诉,而把诉讼化解于前端。
自宋始,至明清两代,随着商业的发展,具有工匠和商人联合协会性质的“行会”随之出现,其产生源于生产力的发展、物质生活和平民生活的丰富。即使在重农主义的官方指导下,城市的行会经济不可避免地涌现了。商事领域中出现了由商人联合自发管理的组织,如商帮、行会、会馆等,对于这些组织内部的纠纷,家族内及乡里的调处的影响力非常有限,也难以服众,也没有解决该类纠纷的能力。要形成组织,必然先有规范,此时行会的领袖就会召集组织成员“公同议罚”,往往在纠纷出现后会依据成本法律、帮规行规、商业习惯进行处理。如有某行会约定:“有事约庙,务须先告管总,与值年首人酌量事当约否,如当约,先送典钱八百文与总首人,总首人宜平心论理,秉公分析,不得树党偏袒。”此处不但记载了早期的仲裁员——总首人,还记载了早期的仲裁费用的缴纳过程,但仲裁费仅用于“摆卖茶食”,类似于仲裁机构的积极花费。行会适用的主要规则——行规,也必须得到政府的认可甚至批准,因为私立行规是禁止的,行规应当与国家的强制性规范和对行业的经营范围规定保持一致性。
在一些国外学者的眼中,清代的行会裁判是比较典型的商事仲裁,具备商事仲裁的典型特点:“调解委员会,有关当事人及证人在一座寺庙见面。在那儿,引发这场纠纷的货物,摆在委员会面前,各方都简短作了证。听了证人发言,经短暂商议之后,委员会作出裁决。双方接受这一终局裁决,站了起来,向委员会鞠躬,彼此相互鞠躬,……倘若告官,……会带来诸多不便。”
商事仲裁在封建制度下的商品经济中初现端倪,显然是具有经济基础决定的必然结果,不会因为土壤的不同而产生区别,但是这种基因体现出的中国因素,是不能忽视的。一方面政府更加依靠组织的自治去解决自身并不关注的私事,以防止过多的精力投入影响了行政的效率;另一方面政府仍然保留着作出最终决定的权力,以防止对社会秩序的失控。这种矛盾的治理观贯穿于中国式的商事仲裁的始终。
三、商事仲裁的中国传统基因
综合上述史料,显然,哪怕在中国长期以来封建社会倡导“重农抑商”“厌诉止讼”的主流思想下,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和商事纠纷仍然有极大的纠纷解决需求,也不可避免地随之产生了半官方授权的或者是商业内部产生行业自治的商事仲裁机制。这些机制很大程度上与欧洲传统的商事仲裁有异曲同工之妙,但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独特的“基因”:
(1)调解和仲裁的不可分离性。“调处”本身是不可分离的,均同等地视为把纠纷消灭在向官府诉讼前端的方式,其价值取向也是完全相同的,调解员和仲裁员实为一体,把调解和仲裁放在同一程序,非常有利于解决纠纷、化解矛盾,虽然客观而言调解员和仲裁员的角色分离似乎更能厘清二者的关系,但放在同一程序也当然地大大提高了解决纠纷的效率。当代中国的仲裁机构多数情况下也把调和裁集于一体,显然,这种基因足以成为中国式商事仲裁的独特优势之一。
(2)来自官方授权的仲裁。抛开封建末期出现的行业仲裁,在传统乡土中出现的仲裁其权力多来自官方正式或非正式的授权。虽然现在认为仲裁权力来源于当事人两造达成一致的仲裁协议条款,但官方的授权可以使结论更具规范性和强制力,能够更好地保证结果的实施。行会仲裁结果的执行多取决于当事人的自律性和对行会规则的遵守,而受官方授权的仲裁却可等同于比照审判机关最终司法文书的效力。强制力对于仲裁结果的保证,正因为这种纠纷处理方式已经得到官方的认可和国家强制力的支持,显然,这种基因对于解释当代的仲裁因何能够得到法院执行机关的实施,更加具有解释力。
作者简介
詹晖|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北京仲裁委员会 / 北京国际仲裁中心仲裁员。
